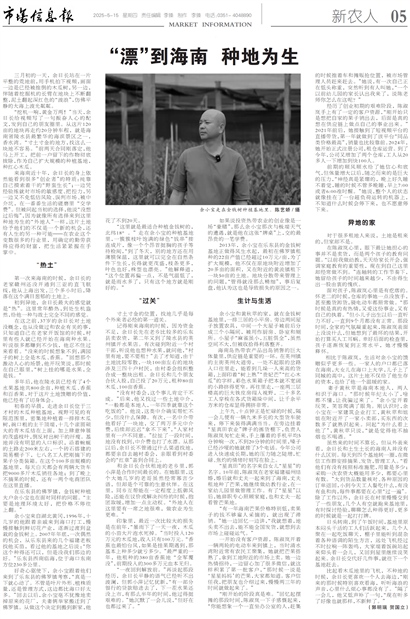三月初的一天,余日长站在一片平整的荒地前,用手机拍下视频,画面一边是已经被推倒的木瓜树,另一边,伴随着挖掘机的长臂在地块上不断翻整,泥土翻起深红色的“波浪”,仿佛平静的大海上波光粼粼。
“挖机一响,黄金万两!”当天,余日长给视频写了一句振奋人心的配文,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。从这片120亩的地块再走约20分钟车程,就是海南省陵水县最繁华的海滨景区之一,香水湾。“寸土寸金的地方,找这么一块地不容易。”前两天合同刚落定,他马上开工,把前一户留下的作物彻底拔除,作为自己扩大规模的种植基地,种红心木瓜。
来海南近十年,余日长的身上依然能看到很多“创业者”的特质:纯靠自己摸索着干的“野蛮生长”;一边凭经验练就对市场的敏感度、把控力,另一边又不免低估风险、误判市场、被中介坑,在一番番生活的磋磨里“交学费”。但被问起当初的选择,他说“没想过后悔”,因为就像所有选择来到这里种地为生的“外地人”一样,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不仅是一个新的机会,还有人生的另一种可能——在农业这个变数很多的行业里,用确定的勤劳获得应得的财富,把生活紧紧握在手掌中。
“热土”
第一次来海南的时候,余日长的老家赣州还没开通到三亚的直飞航线,他从上海出发,三个多小时后,降落在这个满目葱郁的土地上。
初到异地,余日长最大的感觉就是“热”。这里常年酷热,到处生机盎然,给他一种与故土完全不同的感觉。
在这之前,37岁的余日长对土地没概念,也从没做过和农业有关的事,只知道自己在老家开饭馆的时候,村里有些人就已经开始在海南种水果。听说很多都赚到不少钱,他忍不住过来看看。“没来的时候想象不到,满园子的树上全是木瓜、香蕉。”回想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,他开玩笑说,那时候在自己眼里,“树上挂的哪是水果,全是钱。”
多年后,他在陵水县已经有了4个水果基地共800余亩,种植木瓜、香蕉和百香果,对于这片土地馈赠的价值,他已经有了切身体会。
初春的早晨,走进余日长位于三才村的木瓜种植基地,视野可见的有限范围里,密集地种植着一排排木瓜树,碗口粗的主干顶端,十几个滚圆硕大的青木瓜结在上面,加上肆意伸展的茂盛枝叶,倒反衬出树干的纤瘦。基地并没有明显的入口标识,沿着蜿蜒的土路走200米左右,一个砖石搭建的简易棚子下,七八名工人把刚摘下的果子分类装箱。在这个100多亩规模的基地里,每天白天都会有两辆大货车把9000多斤木瓜销往各地;到了晚上不摘果的时候,还有一两个电商团队在这里直播。
在乐东县的佛罗镇,金钱树种植大户余小宝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。“主要是地理环境太好,把价格不停往上翻。”
余小宝来自湖北黄冈,1996年,十几岁的他跟着亲戚来到海口打工,慢慢接触到鲜切花产业,逐渐过渡到盆栽的金钱树上。2007年年底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从乐东县来的几个福建老板找他买苗,看过他的基地之后说:“你这个种得还可以,但是没我们那边的好。”乐东县西南临海,位于海口东南方位230多公里。
好奇心驱使下,余小宝跟着他们来到了乐东县的佛罗镇考察,“真是一下就心动了。不管是叶片外形、植株质量,还是管理方式,这边都比海口好太多。”回去以后,余小宝毫不犹豫地卖掉原来的花厂,夫妻俩举家搬迁到了佛罗镇。从做这个决定到搬到新家,他花了不到20天。
“这里就是最适合种植金钱树的,北纬18°。”走在余小宝的种植基地里,一簇簇枝叶饱满的绿色“钱串”接连成片,像一个个昂首挺胸的孩子等待检阅,“到了冬天,别的地方还在用薄膜保温,这里就可以完全在自然条件下生长,长得就更茂盛,枝条更多,叶色也好,株型也漂亮。”他解释道,“这个位置再偏一点,不是气温低了,就是雨水多了,只有这个地方就是刚好的。”
“过关”
寸土寸金的位置,找地几乎是每个外来者必经的第一道关。
记得刚来海南的时候,因为资金不足,余日长先在老乡比较多的乐东县卖农资,第二年又到了陵水县的英州镇开水果店。有次碰到附近一个村干部,听说他也想种水果,就问他,“村里有地,要不要租?”去了才知道,由于土地比较零散,一块100亩左右的地块涉及三四十户村民,由村委会组织整合成一整块出租。余日长和几个朋友合伙入股,自己投了20万元,租种80亩木瓜、100亩香蕉。
“没有村委会,这个事儿肯定干不成。”后来,他又找过一些土地中介,“一般都是本地人,一年四季就靠这个吃饭的”。他说,这类中介确实帮忙不少,但没什么保障。有次,一名中介带他看好了一块地,交了两万多元中介费,后续却迟迟“拿不下来”,“人家村里有一户不同意。”拉扯了一段时间,地没有找到,中介费也打了水漂。从那以后,余日长不管通过什么渠道找地,都要亲自去趟村委会,亲眼看到村委会的“红章”盖到合同上。
和余日长合伙租地的老乡里,郭小萍是合作时间最长的。在她眼里,这个大她几岁的老哥虽然经常寡言少语,但却是个可靠的生意伙伴。在这里,同乡互帮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风险,还能在议价或解决纠纷的时候,抱团取暖,增加一点主动权。“外地人在这里要有一席之地很难,做农业为生更难。”
印象里,最近一次比较大的损失是在前年,“暴雨下了一天一夜,木瓜的小苗大片泡水死掉。”当时投入120万元的木瓜地,收入只有100万元。“香蕉也最怕台风,如果是挂果期遇到,那基本上种多少就亏多少。”最严重的一年,他租种的380亩香蕉地“全军覆没”,前期投入的300多万元血本无归。
“一夜回到解放前。”再谈起那段经历,余日长平静的语气已经听不出波澜,但郭小萍记忆犹新,“有一部分银行的贷款赔进去了,下一茬水果还没上市,有那么半年的时间,他过得挺艰难的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说,“但好在也都过来了。”
如果说投资热带农业的创业像是一场“豪赌”,那么余小宝那次与极端天气的遭遇,就是他在这张“牌桌”上,交的最昂贵的一笔学费。
2013年,余小宝在乐东县的金钱树基地正做得风生水起,最初在佛罗镇租种的22亩产值已经超过10万元/亩,为了扩大规模,他不仅在原地块附近增加了20多亩的面积,又在附近的黄流镇租下一块50亩的土地。地块分散带来管理上的问题,“管得就没那么精细”,事后复盘,他认为这也是导致损失的原因之一。
生计与生活
余小宝和黄秋苹的家,就在金钱树基地里,一排三居的小平房。旁边两间屋子放置农具,中间一个大屋子被前后分成三个小隔间,被用作厨房、卧室和厕所。小屋子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虽然空间不大,但被收拾得利落整齐。
海南岛热带农产品出岛销售的巨大体量里,供应链是重要的一环。在英州镇的主街英州大道旁,一处不起眼的岔路入口往里走,能看到几垛一人来高的货箱,上面印着“树上熟”“贵妃芒”“红心木瓜”的字样,彩色水果箱子把本就不宽阔的小路挤得更窄。再往里走,一座两三层楼高的巨大铁皮房闯入视野,二十多名工人穿梭在各式货箱垛中间,让千余平方米的仓库显得拥挤非常。
上午九、十点钟正是忙碌的时候,隔一会儿便有一辆九米多长的大型货车驶来,停下来装得满满当当。在旁边挂着“星真田农业”牌子的拣货棚下,负责人陈淑岚匆忙走来,手上攥着的手机平均5分钟响一次,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,嗓子已经沙哑的她就接了3个电话。今年公司进入快速成长期,她的压力随之陡增,忙碌、焦灼的情绪时刻写在脸上。
“星真田”的名字来自女儿“星星”的名字。10年前,陈淑岚在老家福建福州结婚,婚后就和丈夫一起来到了海南,丈夫租地种了芒果,她继续做幼教行业,在一家幼儿园里做管理工作。有了“星星”以后,她辞职专心照顾家庭,也和丈夫一起看管芒果地。
“有一年海南芒果价格特别低,卖果子的钱不够雇人采摘的,就出现了滞销。”她一边回忆一边讲,“我就想着,地头卖不出去,能不能全国发货,就想到去市场上碰碰运气。”
一开始没有客户资源,陈淑岚开着一辆两轮的电动车来到镇上,当时清水湾附近常有农民工聚集,她就把芒果捂熟了,拿到工地附近的市场上卖。她一边热情招待,一边留心加了很多微信,就这样积累了第一批客户,“那时候一说是‘星星妈妈’的芒果,大家都知道。客户信任我,把朋友也介绍过来,慢慢两三年的时间就做起来了。”
“刚开始的阶段真是难。”回忆起摆摊的那段时间,陈淑岚一下子感慨起来,“你能想象一个一直坐办公室的人,赶集的时候推着车和摊贩抢位置,被市场管理人员赶来赶去。”她说,有一次自己正在低头称重,突然听到有人叫她,“一个以前幼儿园的家长认出我来了,说陈老师你怎么在这呢?”
经历了创业初期的艰难阶段,陈淑岚手上有了一定的客户资源,“刚开始只是想把自家的果子销出去,后面是真的想在供应链上做点自己的事业出来。”2021年前后,她接触到了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货,第一年就做到了该平台“同品类价格最高”,销量也比较靠前。2024年,她开始正式注册公司,租仓库运营。到了今年,公司又增加了两个仓库,工人从20多人一下增加到快100人。
前期的顺风顺水给了她信心和底气,但体量增大以后,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压力,“神经真是紧绷的,晚上好久睡不着觉,睡的时候不管多晚睡,早上7:00或者6:00准时醒。”她说,整个人的状态就像挂在了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上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,也不愿意停下来。
异地的家
对于很多租地人来说,土地是租来的,但家却不是。
在陈淑岚心里,眼下最让她担心的事并不是卖货,而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。“以前我做幼教,天天给家长开会,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,现在到自己这里却经常做不到。”连轴转的工作节奏下,她留给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,不由得生出一股由衷的愧疚。
面对孩子,陈淑岚心里是有疙瘩的。怀老二的时候,仓库的事她一点没放手,甚至搬货卸货,骑电动车都照常做。“那时候是真的有热情,又爱这份事业,又有自己的执着。”但小儿子出生以后一直听力不好,一直到9个月都没有正常。那段时间,全家的气氛凝重起来,陈淑岚表面上没说什么,但她想到了最坏的结果,开始打算买人工耳蜗。幸好后面的检查里,孩子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,她才慢慢释怀。
相比于陈淑岚,生活对余小宝的馈赠似乎更多一些。一家人的户口都已落在海南,大女儿在海口上大学,儿子上了同城的高中,这片土地不仅给了他生存的资本,也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。
妻子黄秋苹是海南本地人,两人相识于海口。“那时候年纪太小了,啥都不懂,让我骗过来了。”余小宝开着玩笑,笑容爬满了眼角。刚认识时,余小宝在一家建筑企业打工,黄秋苹和姐姐在附近开了一家小卖部,买东西的次数多了就熟识起来。问起“为什么看上他了”,黄秋苹只说,“就是觉得他不抽烟也不喝酒。”
虽然来的时间不算长,但从外表来看,余日长和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每天到四个基地转一圈,在微信工作群安排摘果、发货,管理工人。“看他们有没有按照标准施肥,用量是多少;采购一次农资大概能用多少,都要心里有数。”大到货品数量核对、各种原因的订单退回,小到今天工人餐吃什么,有没有鱼和肉,每件事都要在心里“过一遍”。
除了工作以外,余日长在村里慢慢交到了一些朋友,几个人有空就跑来基地里,有时探讨经验,聊聊怎么种得更好,更多的时候就是一起打打牌。
日头转南,到了午饭时间,基地里原本闷头干活的工人们活跃起来,几个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,棚子里能听到混杂着各种语调的陌生方言,远处飞机经过不时拉响一阵轰鸣,大家端着饭碗站起来仰头看一会儿,又回到屋里继续说笑起来。余日长交代好几件事,就往下一个基地赶去。
比起看木瓜地里的飞机,不种地的时候,余日长更喜欢一个人去海边,“刚来的那时候特别喜欢看海,听听海浪的声音,心里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。”隔了一会儿,他又低声补了一句,“现在听多了好像也就那样,不新鲜了。”
(郭明瑞 贺国立)